有没有一首歌 ——写在母亲节 ·《遇见》系列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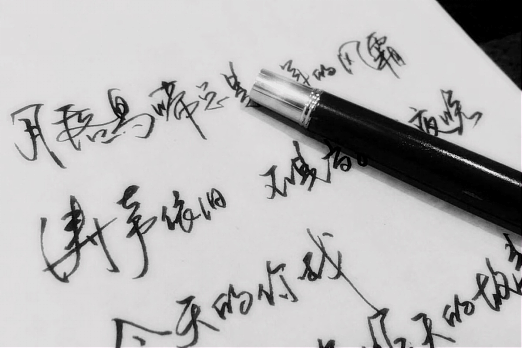
行走,便会遇见; 当擦身而过的美映入心窗,慢慢沉淀,沉淀,久而久之便沉淀出属于自己的荷莲。
夜初上,月雪亮得饱满,一如往常陪着孩子们在街区的四角晃呼啦圈般的兜着圈子,都是这疫情闹腾的,离开家两个街区便乏了安全感。若不是孩子们追着问刚刚唱的是什么, 还真没意识到竟情不自禁的哼起了首几十年前的老歌。“啊月亮,在那高高的天上,你失去了什么,为什么那样悲伤,是不是也没有妈妈,就像我一样……”, 九十年代电视剧《小龙人》的插曲。呵!这曲调怎么就这般不由自主的流淌了出来?我想我应该是想妈妈了,想家了……
深吸了口微凉的空气,抬头望向星宇的无尽, 北斗星所指的故乡向暑的步子紧凑而平稳,南半球的落叶也已然昭示着冬的来临。这许多年,日复一日匆匆的忙活着,陡然间歇了下来看似有了大把的时间,可这心却总是惴惴不安…… 都说是睹物思人,我这人天生细腻敏感,也无需盯着个什么物件儿,一行诗一个旋律便能激荡起思绪的涟漪久久不肯褪去。瞧,散步这一路,心事便翻来覆去没个消停。
【那个夏、那座城、那一位探窗盼归的母亲】
此刻的美国东海岸应该是晨光乍现了的,也不知道身在纽约的丁爸爸可好,会唱歌的“丁爸爸”是孩子们给旅美男中低音歌唱家丁羔先生起的,丁先生很喜欢这个昵称,我便也随着孩子们一起叫了。和先生都是苏州河旁长大的,见面一提到儿时在上海大厦后巷里的故事就关不住话匣,他说那些年顽皮,总偷偷跑到苏州河里游泳,生怕妈妈惩罚,总是兜着圈子把自己晾干了才敢回家,妈妈不管多晚都在窗边探出半个身子等待。我说,外白渡桥的漫步是我和妈妈为数不多的记忆中弥足珍贵的,知青岁月给了我们太多聚少离多的牵挂。话说到这儿,出租车已经稳稳的停在了上海音乐厅的门口,那是一六年的夏末,和先生一起受邀上海电视台的演出。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火热的赤子心灵” 交响初起,后台的我便已热泪满盈,直至曲尽还没缓过神来,无意中和退场的丁先生撞了个满怀。他红着眼眶,见我却步的欲言又止,绅士般的喃喃致歉:“对不起,对不起,情绪有些失控,有些失控。上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在台下,而今她已不在了” ,还未来得及等我送出半句安慰,低沉着头的背影便消失在走廊的转弯处,他哭了… … 我的眼便再也承不住汪洋的重量,蜷缩在角落里成个泪人。此后这首歌便定格了我对那个夏、那座城、那位探窗盼归的母亲永远的记忆。
… …
【一首歌、一众亲、一盏昏黄旧灯守望的阶梯】
“哈喽,哈喽,琳琳!”宁宁姐的电话,突然打断了我的忧思,熟识她的人定是能即刻回想出她独具特色的两声“哈喽”,快乐俏皮永远尾随着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我发了个视频给你,王宏伟问你好呢。还有于文华,侯耀华、刘和刚、祖海……”她一口气报出来一长串耳熟能详的艺术家,这都哪跟哪啊?除了王先生我是熟识的,其他的人对我来说都是天外来客般的遥不可及。挂了电话看过视频后,方才明悟了宁宁姐的欢欣,原来由她作词,澳洲群星演唱的《让爱回家》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国的艺术家们便通过视频短片的方式遥寄对澳洲朋友们的祝福,用以回应这首感人至深的音乐作品。
对于我这个不喜欢用华丽辞藻浮夸事物的人来说,用了“感人至深”这个词,只因深知时逢澳洲各界朋友们为武汉竭力奔走,澳洲疫情一触即发的时刻,创作是无比艰辛的。且不去说艺术顾问纪连祥先生来澳探亲困步悉尼,作曲家周曼丽女士身处武汉的风暴中心,就说我所熟知的朋友建文,悉尼生根的武汉人,年前女儿回国探亲被困,突如其来的心梗让建文两岸牵肠的日子更是步履维艰,在得知作品的消息后,坚持拖着初愈的身体参加排练和录制,我跟他说悠着点,他总说:“没事儿,我行!”。平日的微信里,但凡看到我的帖子与医疗相关,他都在最显著的位置大大的点上几个赞,偶尔留个言:“出不得门,出不上力,就给你们加油,感谢你们为我的家乡做的努力。” 陈建文,当年那个用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唱到爆场的歌手,而今用《路在脚下》《永远的记忆》砥砺前行的男高音。
不觉间回到了家,孩子们头也不回的冲进屋内,争抢着水龙头,一边洗手一边唱起了生日歌,自从疫情开始这首歌便不时回荡在四方的天空里, 也算是各自为政的安居生活最雀跃的调味品。 独坐在廊灯微醺的阶梯上,再次播放了一遍视频,艺术家们熟悉的面孔诚挚的表达着对澳洲朋友们的祝福,仿佛就真的是个老朋友,坐在身边和自己聊上那么两句,愁绪竟也转瞬间不翼而飞。都说幸福是会传染的,翻出了那首让爱回家的伴奏带,煞有介事的唱了起来“多想把你拥抱,为你点亮希望……” 是啊,一首歌真的能让一个人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驻留很久,董宁、《让爱回家》、悉尼的群星就这样让我记住了这个不凡的秋殇里有爱的蔓延。
【敞篷卡、摩天轮、柠檬树下咏叹的诗句】
2020年5月9日 晚9点 澳大利亚
一诺,尤克里里女孩,墨尔本(维多利亚)
一诺:“妈妈,我能唱你写的那首歌吗?”
行悦:“唱吧!”
一诺:“什么是钟馗?”
行悦:“伏妖降魔,抓鬼怪的”
初见一诺,在上海, 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们围坐一桌,她竟没有半点拘谨,说唱就唱的来了一首《柠檬树》,她说要是有尤克里里在,会唱得更好。 再见一诺,长大了许多,硬是扛着大大的吉他走上了悉尼的舞台,为我们庆祝新书的出版,母亲行悦是新书的主编。不管时光如何变迁,她的个头如何赶超了我的,在心里,她就是那个无拘无束,可爱的尤克里里女孩。你听,她又开始唱歌了!
张军,歌唱家,帕斯(西澳)
敞篷卡,上个世纪的古董了,今夜后厢的平台便是他的舞台,此刻繁星为景,流云似幕,配乐响起,一棵老树的枝丫随风轻和着旋律跃跃欲试的要和他赛上一曲弄臣里的咏叹,可没等张军开口,老树便打了退堂鼓,它说他是西澳的波切利。
观众因社交距离的惯性三三两两的散坐着,但绝不失礼的在曲尽之时报以热烈的掌声。签约西澳歌剧院的著名歌唱家张军和艺术家们就是用这样温暖的形式,开着敞篷卡用音乐把我们带进了亦真亦幻的梦里。
深夜聊歌剧聊孩子也没个正题,他说能喝上几杯自己是“酒八级”,我说师妹在下有礼,也能喝上几杯是“酒九级”,于是两个人都会意的笑成了个孩子。
他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唱了两首中国的艺术歌曲是给导师和自己留个念想,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普契尼;我说还是最喜欢你唱《喀什葛尔女郎》,带着那条深爱着的中国红围巾。
是啊,那一条中国红的围巾!

奥斯卡,RAP迷粉,布里斯班(昆士兰)
昆士兰的摩天轮下, 拐角名叫CHAMP的西餐厅,地标。“厅主”奥斯卡并没有因为多日的“暂停营业”而沮丧,又在微博上评酒点菜,贫嘴耍酷;古诗今辞鱼贯而出,逗哏打趣不亦乐乎。
“金气秋分, 风清露冷秋期半。正是“仗酒祓清愁, 花销英气”的季节,下厨把蔬菜切成花的形状,做几道简单的家常,使忧伤的心绪安静下来。无论什么都不放心上!佐以御兰堡酒庄这一款深邃复杂的混酿——The Signature Cabernet Shiraz(红酒用词),口感饱满且丰富,夹杂着黑李子, 胡椒和甘草的复杂香气,搭配脆嫩且味道咸香的蔬菜更是令人口齿生津, 可谓“且须饮美酒, 乘月醉高台”。 其实我什么都没做, 可我此时却感到心境优雅, 灵便轻松”
“HoldOn(等等)
艺术点亮了生命的长河
表达的方式不同但拒绝隔阂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发现那是白费口舌
喜欢偶尔片刻间那种单纯的笨拙
每个人都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烟火”
艾琳,诗人,悉尼(新南威尔士)
“在诗里我是自由的,星宇在心底尽情流转,渴望在梦中无畏的释放,傲然在浩瀚中肆意游荡…… 每一个夜晚都似昨夜的反复,执笔,那支老旧得脱了漆的深蓝色钢笔,比比划划不肯停……” 我的笔体, 老旧得形同那支钢笔。诗人说:“你语言休克了!我们喜欢的是那个能把一桌子人掀翻的艾琳,把你活脱俏皮的乱语写成诗,才不枉在落笔中来去!”
拿起手机打了四个字“断笔志异”
“ 向晚的风又吹了,发丝落在一页纸上
本拾起,犹豫了片刻;夹留在缝隙里吧!
不日回窥的青春有乌黑的色
值不值得说的人,也没有名字;画了个圈深不见底,那就是心吧, 青葱的
有个声音,留下一首歌,一个少年走过… …”
【灯熄灭了,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将儿子的房门半掩,和女儿道了声晚安,先是赶进客厅收拾残局,再是下了厨房,盘算着明日的三餐。夜深,端着本穆旦的诗文集子发呆,脑子里竟然映着的都是胡适散文《母亲》中的片段。
“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掀开窗帘,月还在,想起十几岁独自在上海求学时和母亲通信,她总是在信尾写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生怕我看不懂,在婵娟的后面加了个括号标注了“月亮”二字。她说他那时人清秀,文笔好,人家都叫她诗人,我说“我也要做诗人!”;她说每个人都会结婚,我说“那我和你一起结婚”;她说她想我了就看月亮,我说“那我也看!”…… 于是《望月》便成了那首会让我想起母亲的歌。
“月亮在天上我在地上,就像你在海角我在天涯
月亮升得再高也高不过天啊,你走的多远也走不出我的思念
… …”
“灯熄灭了,月亮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 … …”
是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想起二零二零一起的走过… …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