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下中国快要消失的手艺,却被20家电视台拒播,只因镜头下的人太过真实(组图)
这是一部“非主流”的纪录片,
一拿出手就被二十多家电视台拒播,
就连导演本人对纪录片的评价都很令人绝望:
“一、土得掉渣;
二、摄影和录音师毫无经验;
三、没有导演技巧;
四、音乐单一……”

连海报,都透着一股子草台班子的味道
可这么一部“奇葩”纪录片,
最近却在B站大火。
10天里点击量超过7万,
在豆瓣也拿下了8.7的高分。
很多人直接看哭,
甚至两天后跑来再看第二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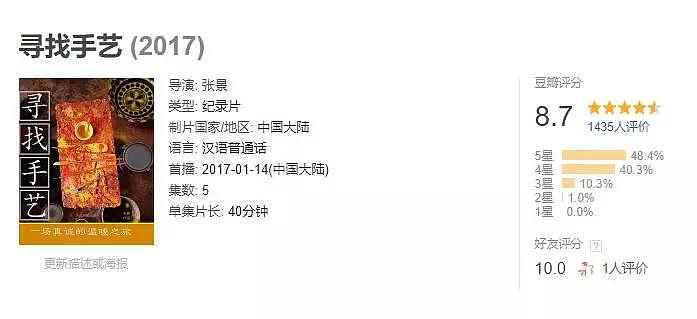
“朴实,温暖,接地气”
是评论里出现得最多的词,
因为《寻找手艺》的镜头里,
记录的就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民间手艺人。
他们的人生很慢,
慢到做好一件事,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
然而,
如果不快一些记录他们的人生,
可能就来不及了。

在云南,
导演第一次在拍摄时留下了眼泪,
因为一位80多岁的做伞老人——坎温。
他几十年如一日,
每天都靠在墙角做伞。

拍摄期间,
老人用棉线固定伞骨架时,
线断了8次。
每断一次老人都会愣神,
然后焦急地尝试下一次,
到后来变得十分沮丧。
导演说:
“说起来也没什么好哭的,
但是我就是每看一次,
就哭一次。”

一把伞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所有材料就是竹子、纸张、棉线,
坎温做伞都是凭几十年的感觉,
但是他 ,
终究还是老了。

今年4月片子上传到B站之后,
有人给导演私信说想买老人家做的伞。
导演统计了一下大概有20把,
联系坎温家人时,
他们说坎温今年2月已经去世了,
再也没有人做伞了。

在贵州小黄村,
两位老奶奶正在用极其简单的方式造纸,
那也是她们人生中最后一次手工造纸,
她们打算把剩下的原料全部用完就不再做了。
这也意味着,
当地的造纸术或许也随之失传。

在拍完造纸后,
导演要记下她们的姓名,
还给她们拍照。
脸上满是皱纹的两位老人都特别高兴,
笑容满面地说:
“这下我们的名字到北京了,
照片也到北京了,
就算名字到了北京也好啊。”

两位老人静静地造了一辈子的纸,
在收工时知道名字和照片被记录下来,
就已经像孩子一样心满意足。
纪录片在B站发布后,
大家在这段的弹幕里密密麻麻写着:
“阿妈,你们到北京了。”
“已到上海”
“已到广州”
“已到纽约”
..........

在新疆喀什,
做陶器的吐尔逊江大叔说,
他家的房子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开发商要征地,
给他12套单元房他不要。
他不在乎赚钱多少,
只想给世人留下更多的陶器。

他说:
“祖辈留下的房子不能在自己手里毁了,
祖辈的手艺也不能在自己手里毁了。”

做陶器的时候,
大叔一直在土窑里专注地爬上爬下,
但当他把最后一批陶器送入火窑后,
大叔却突然对着镜头开始发起了牢骚。
他担心,
有一天他不在了,
这些陶器就会慢慢消失。

在西藏,
这个21岁的帅气小哥,
从13岁起就开始刻经了。

当摄制组问,
是不是刻得越多,拿的钱就越多?
他连忙摇头说:
“不是不是,刻的时候好好刻,
慢慢刻,对这个板子好一点嘛,
否则良心过意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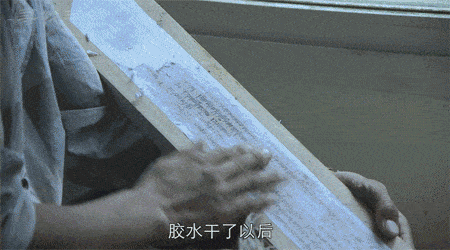
从18岁开始编制腰带的石大姐,
四十多年从未间断。
每年能编出5-6条,摆到集市上去卖,
开价100。
往往会被人砍到65至80,
问到编织腰带累不累、难不难的时候,
石大姐给出了毫不犹豫的答案:
“会就不难,不会就难;
喜欢,所以不觉得累,不喜欢才会觉得累。”

在山东泗水,
导演还拍摄了土陶的手艺人刘新文,
在他的门口贴着一张显眼的字条,
姓名后面特意标注了“末代传人”四个字。
他之所以称自己是泗水陶器的末代传人,
是因为柘沟镇曾经有几百户人家制作土陶,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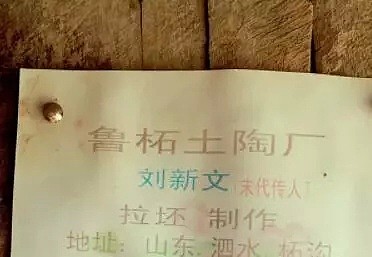
在片子的后期剪辑中,
导演却犹豫着没有把刘新文放到正片里,
“他几乎是中国传统手艺和手艺人的一个缩影,
可是,太悲凉了,
看到他,心里总会有一些没落的寒意。”

在四川喜德县,
当地最大一家漆器厂已经倒闭了,
这里曾以彝族漆器闻名。
只用红、黄、黑三种颜色组合,
就能勾绘出色彩明丽的器皿。

吉伍五各是吉伍家族漆器的唯一女继承人,
六七岁开始喜好漆器,
在父亲的细心传授下,
手艺已经远超前辈。
然而现实打败了喜德县的漆器厂,
也打败了吉伍五各。

漆器厂倒闭后,
父亲不敢再让女儿受生活之苦继续漆器之路。
他让女儿去考了老师,
如今成了小学老师的吉伍五各,
只能在周末和节假日回来帮帮爸爸的忙,
但她告诉导演,其实她最深爱的还是漆器。

四川荥经,
这里的砂器看似供不应求,
但愿意接单的人却越来越少,
“货主把价格压得太低了,
每一只砂器的利润到了手艺人手里,
只有不到1块钱。”

即使是在商铺林立的砂器一条街,
手艺人已经从百十号人降到20多,
且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
因为利润太低,
年轻人无人能静下心来做砂器,
在火烫的砂窑里,
热得满头大汗的大哥说:
“再过十年二十年,荥经砂器就该灭绝了。”

戈壁荒滩上,
摄制组找到了胡大拜尔地,
他在很远的地方放羊,
看到有客人来他特别开心,
把家里的鸡蛋煮了一半。

他是牧羊人,
也是民间艺术家,
他的音乐撼动人心,
会制作、演奏巴拉曼、热尔普、都塔尔等民族乐器……

“向北90公里无人,
向南8公里无人,
向西11公里无人,
唢呐的声音以胡大拜尔地为中心,
抚平整个戈壁滩。”

然而,
胡大拜尔地的手艺却当场失传。
他的儿子没有学习做乐器,
连一个音符也吹不响。

这些手艺人,
用苍茧与汗水,
讲述了他们一生的故事。
也用一生的时间,
经历了传统手艺“从有到无”的过程。

他们从不问什么是工匠精神,
只是单纯地埋头工作。
导演说,
在拍完这个纪录片之后,
他觉得很惭愧,
“再也不好意思提梦想这个词了。”

虽然一开始,
他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去拍片就是因为梦想。
因为预算有限,
请不起专业人士,
不仅摄影师是由司机临时担当,
录音师还得兼职灯光,外联,
拍摄设备是二手的。

导演不仅跟着摄影还亲自做后期,
拍完剪了50多遍,
成片后也没钱做推广。
“一般电影至少几十万几千万的推广费,
但我一分钱没有。”

被电视台拒播,
《寻找手艺》连成本都收不回。
但导演却表示:
“有人看就好,
拍出来没人看才惨,
用一套房子,
为100多位手艺人留下了影像记录、文字记录,
值了。”

“一门手艺的消亡,
就代表着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消失。”
手艺人的坚持,
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对文化传承的守护。

我们无法阻挡时代的变迁,
只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手艺人。
也许关注的人多一些了,
手艺就能消失得慢一些,
再慢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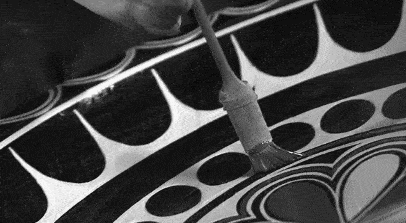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