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要求最高法道歉 丢的卷宗隐藏什么秘密(图)
2018年12月30日,《华夏时报》深度调查部公布了其收到的一段疑似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林清的自述视频,王在视频中讲述,他曾作为陕西榆林凯奇莱公司诉西安地质勘察院案件承办人,在准备写判决书前发现原存在自己办公室的案卷离奇被盗。王表示,“我想通过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要给自己、为保护自己,免遭不测,留下一些证据。”
此前一日,崔永元在微博上质疑“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在审理机关丢失,崔永元的微博截图显示,2016年12月2日,发现凯奇莱一案的二审卷宗及二审开庭笔录的电子版均丢失,崔永元还爆料,高法合议庭还被要求补签一份凯奇莱案2013年中止审理的合议笔录。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微博发布情况通报:其中两张图片所载内容与目前保存在最高人民法院档案处的有关内容相同,已经启动调查程序,欢迎崔永元教授等知情人提供情况。如发现我院工作人员违反审判纪律问题,将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发生在2003年的陕西榆林凯奇莱公司诉西安地质勘察院案,因被曝出案卷在最高法办公室离奇失踪而再度引起关注。早在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就在以《“黑金”争夺战》为标题的封面报道中对此案进行了详细报道。
此案从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简称“西勘院”)2006年11月对陕西高院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到最高法做出二审裁定,隔了整整三年。其间,陕西省政府和最高法的不寻常互动引人关注。先是2008年4月,最高法时任副院长奚晓明邀请陕西省政府相关负责人到最高法“商议案情”。
接着,2008年5月,陕西省政府提交给最高法一份报告,名为《关于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探矿权纠纷情况的报告》,其中的一句话引发了广泛质疑,即“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
2009年11月,最高法作出二审裁定,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2011年3月,陕西省高院重审此案,判决西勘院与凯奇莱合同无效,即推翻了自己此前做出的判决。
而在此案重审前后,陕西省相关部门对凯奇莱公司和赵发琦进行了调查。2010年8月21日,该省榆林市工商局以虚报注册资本为由,对凯奇莱公司罚款5万元;2010年至2011年,陕西省工商局先是撤销榆林市工商局的处罚,随后决定注销凯奇莱公司的工商登记。
2011年8月19日,榆林市公安局拘捕了赵发琦,理由是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在看守所待了133天后,赵发琦被取保候审,后被判无罪。此后,也就是在2013年,赵发琦再次将该案上诉至最高法。与此同时,他公开举报了多名官员。
2017年11月,西勘院原院长陈磊被调查。此前,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王登记、陕西省地矿勘查开发总公司原董事长梁枫等人也被调查。
早在2015年7月,最高法原副院长奚晓明被调查。2017年2月16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对被告人奚晓明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奚晓明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奚晓明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据凯奇莱法律顾问、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长透露,2017年12月21日,最高法以约见谈话的形式下达了判决书,终审判决凯奇莱胜诉,凯奇莱与西勘院的合同有效。此时,煤炭的黄金十年早已过去,而涉案的煤矿至今空闲在毛乌素沙漠里。
在最高法办公室里离奇丢失的案卷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请看《中国新闻周刊》8年前对此案的详细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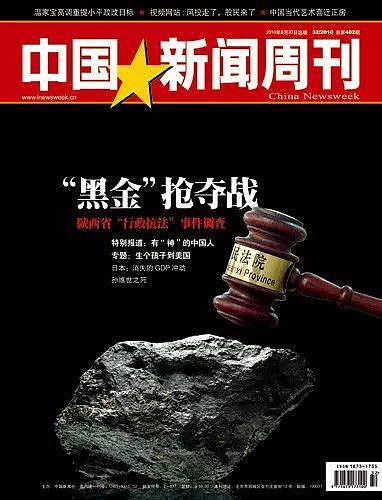
中国新闻周刊2010032期封面:“黑金”抢夺战
“黑金”抢夺战
陕西省“行政抗法”事件调查
陕西省人民政府密函施压最高人民法院,一时引起公众瞩目。1949年以来,首次披露的中国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最高层级的对抗背后,到底是什么呢?
是煤,是蕴藏在陕西榆林——这片中国传统的贫瘠不毛之地下面的价值千亿人民币的黑色金子,催生了这幕情节曲折,关系错综复杂的悬疑推理剧。
《中国新闻周刊》几路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当地近期发生的两起矿权纠纷,起因不在于法律不健全,而是因为部分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深深卷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商业博弈中。
“密函施压最高院”背景下的陕西矿权纠纷调查
在赵发琦和刘娟争夺波罗矿井产权的过程中,可见幕后运筹的隐形力量
本刊记者/申欣旺 (发自陕西西安、榆林)
“陕西省密函施压最高院”事件背后所涉案件有了最新进展。《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来自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延长石油”)的合同文本显示,“密函事件”利益相关当事方,陕西省十一五重点项目——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股权正在发生变化:中化益业旗下240万吨/年甲醇MTO项目将由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2亿元持股51%。
合同的双方力量悬殊,引人关注。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乃大型国有企业,是国内拥有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资质的四家企业之一,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806.28亿元、利润50.15亿元,上缴各级财政税费273.9亿元。而中化益业注册资金2亿,2006年纳税116730元,2007年全年未纳税,2008年全年纳税42061.12元。
按照合同,通过此次转让,中化益业将通过一处权属尚存争议的矿区以及并未建设的重点项目,获得超过1亿元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将直接进入陕西益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陕西益业)账户而并非中化益业。
知情人士称,由此合同可见中化益业的急迫“套现”心理。2003年陕西省政府曾规定,“对已配置资源但又不能如期进行(甲醇)MTO项目转化的项目,省政府将无条件收回探矿权和采矿权。”陕西省发改委亦曾发文明确,未能如期转化将收回配套资源。而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一期建设周期为2006年至2009年8月,在此期限内未进行MTO项目转化。
圈煤迷幕重重
在这份“关于中化益业的股权转让合同”中,转让方陕西益业同意延长石油持有中化益业51%的股权,中化益业的另一股东陕西太兴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太兴置业”)则完全退出。
双方约定,延长石油分批次将资金汇至陕西益业账户。陕西益业并保证其“对所转让的股权及公司资产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或其他限制权力的情形及相关争议纠纷”。
延长石油一位接近决策层的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合同在2009年12月签署,并上报延长石油主管部门陕西省国资委审核。但由于延长石油内部有人质疑该项转让将国有资产流失,导致项目未能如期进行。
据了解,延长石油内部反对者认为,股权转让涉及巨额资金,中化益业煤化项目是否投资建设本身就是个问题,评估资金还如此之高,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其他渠道证实,这位员工所称的“评估”是指,早在2009年5月,中化益业、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有限公司和延长石油委托陕西正德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榆横煤化学工业区一期在建项目和榆横矿区波罗煤矿在建工程进行资产评估,以便为双方的股权转让合作提供基础。
在两份分别厚达数百页的评估报告中,评估公司提出,评估所使用信息均由委托方提供,并假定所有信息真实有效。
两份评估报告显示,委托方即上述三家公司分别承诺,报告所涉及的的土地使用权证无纠纷;而陕北榆横矿区波罗矿井探矿权为委托方购买取得,探矿权证正在办理之中,产权无纠纷。
事实则是,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配套煤炭资源波罗矿井本身即处于争议之中。此外,多种证据显示,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本身也处于开工未建状态。
早先,中化益业曾意图在项目获批之后直接建矿井采煤。2006年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开工典礼之后,建筑队就开进了波罗矿井,并建成分别深400米的采矿井两口。
榆林当地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煤化项目未建而矿井先期开工,圈煤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但采煤行动最终却因为波罗矿井权属司法争议另一当事人赵发琦的介入而终止。
赵发琦所拥有的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凯奇莱)正是波罗矿井“一女二嫁”权属未定司法纠纷中的当事方。
2003年8月,拥有波罗矿井采矿权的陕西省地矿局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下称“西勘院”)与凯奇莱签订《合作勘查合同书》。双方约定,凯奇莱支付西勘院前期勘探费用1200万元,后者同意前者拥有该普查项目勘查成果80%的权益。
但随后,西勘院突然通知凯奇莱,以“合同内容与2003年10月2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的21次会议纪要有关政策不相一致”为由,表示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实施,不收取约定费用。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21次会议纪要”是指2003年10月22日陕西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对省政府前几年已给予一些煤田探矿权的单位,一律视作代表政府实施地质勘查,探矿权人无权处置矿权,其探矿权是否转让、转让给谁,如何转让,一律由省政府根据基地建设总体规划和转化项目落实情况作出决策。
是次会议明确,“对在陕北已落实的MTO转化项目,由省政府统一配置相应的煤炭资源”。由此,MTO转化项目成为获得煤炭资源的敲门砖。
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正是中化益业拿到的敲门砖。作为配套资源,“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得到面积多达340平方公里的榆横矿区波罗矿井。2006年的勘探显示,该井田各类资源量超过20亿吨,以市场价计算,价值惊人。
该项目一期60万吨甲醇工程2006年6月正式开工,让中化益业公司董事长刘娟“面子”有光的是,多名中央和陕西省政要出席了开工仪式。根据官方文件,项目应该于2009年8月建成投产,总投资23亿元人民币。
但正是这一“已经”投产的重点项目引发了广泛的质疑。知情人士说,该项目自开工典礼之后,从未真正在MTO转化项目上进行过建设,所谓“投产”不过是写在纸上的谎言。
多种证据表明,该重点项目开工后并未建设。这种观点亦在官方得到证实。《中国新闻周刊》获知,该项目在2006年、2007年连续列入陕西省重点项目年度计划,但在计划竣工年度却不见踪影。对此,陕西省发改委主管“转化”项目的石油天然气处人士表示,重点项目在无法正常推进的情况下将从年度计划中拿下。
榆林市发改委一位官员亦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自2009年后,就处于停建状态。”
“一女二嫁”风波未息
在西勘院通知凯奇莱公司表示因与陕西省政府“21次会议纪要”不符,“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实施,不收取约定费用”后,赵发琦给时任省长陈德铭写信反映问题。
在陈德铭的过问下,陕西省政府责成省国土资源厅协调,最终形成了2005年11月8日作出的陕国土资办发[2005]65号《关于协调解决榆林市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炭资源合作勘查争议情况的报告》,报省政府办公厅。
在该报告中,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认为,“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双方承诺愿意承担风险,也愿意按照陕西省政府有关规定进行合作勘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可同意其合作勘查。”
但就在刚做出上述协调处理意见两个月后,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报送“关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化学工程”)、香港益业投资有限公司(香港益业)参与波罗井田煤炭资源勘探工作协调意见的请示”。
“请示意见”中提出:“按照中国化学工程和香港益业出资,西勘院负责勘探工作,勘探成果归出资人所有的原则,待‘甲醇MTO项目’经主管部门核准立项后,由西勘院依法将该井田探矿权转让给项目开发业主。”从后来的系列文件来看,煤化项目与煤炭资源各自的开发业主正是与中化集团、香港益业都无关系的中化益业以及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有限公司。
“波罗井田”面积约340平方公里,而赵发琦与西勘院持有的“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矿普查”探矿权,在波罗井田范围内的面积约为258平方公里。实际上意味着,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合作勘查区域大部分落入其中。赵发琦的说法是,当时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前期合作已经探明煤炭储量惊人,被对方看中其中价值。
此后,形势对赵发琦越来越不利。即便是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向省政府进行上述请示时,时任省长陈德铭仍批示“原西勘院与凯奇莱的纠纷请妥处”。
但显然,矛盾并未被“妥处”。2006年4月14日,在与凯奇莱的合同未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西勘院与刘娟担任法人的“香港益业”签订了关于“波罗井田”的合作勘查合同书。
当年5月,凯奇莱将西勘院起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随后,陕西省高院一审判决凯奇莱胜诉。陕西省高院认为,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双方所签订的2003年8月25日合作勘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同有效。”
随后,西勘院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这意味着,争议矿区仍处于权属待定状态。但就在二审期间,陕西省政府以密函送达最高院,函中称“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
赵发琦怀疑,此举有猫腻。国家发改委2006年对陕西省发改委“关于开展横榆矿区波罗煤矿建设前期工作的请示”复函显示,该矿为“增强煤炭供应能力,满足国民经济对煤炭的需求,同意开展前期工作。”
赵发琦据此认为,“虽然省发改委不愿公开请示函,但从复函可以看出,项目并不是以MTO转化的名义进行申请,而是偷梁换柱成了‘增强煤炭供应能力’,这明显是有关部门在协助圈煤。”
2010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探访横山波罗矿井区,发现只有看护矿井人员所住的简易房、两眼矿井与毛乌素沙漠的黄沙为伴。
隐者刘娟
这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女人
本刊记者/王维博 申欣旺(发自西安)
刘娟何许人也?她为何有如此能量,从半途杀出,搅了赵发琦的发财美梦?
虎口夺食,取代赵发琦的凯奇莱公司,与陕西省地矿局地质矿产勘察开发院签订新的合作勘查合同,将陕西省榆横矿区340平方公里地下近20亿吨、估值近千亿元人民币计的煤炭储量轻入囊中的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娟,而中化益业的大股东陕西益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为刘娟。同样是这个刘娟,还是注册资金为100万港币的香港益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陕西省国资委主管的和谐先锋网相关资料称,刘娟具备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极强的资本运筹能力。不过,这位关键的操盘手极为低调,很少见诸媒体报道。
还是这个刘娟,当中化益业公司波罗井煤化工项目陷入司法纠纷,几无进展之时,又与大型国企——陕西延长石油集团签署股权转让意向。收取过亿元的股权转让费,意图抽身。而这每一步,都显露出刘娟非同常人的进退有据,腾挪自如。
3个“益业”?
围绕陕西榆林波罗矿井产权纠纷,先后出现的3家名称中包含“益业”的企业,背后均指向“女港商”刘娟。
最早的一份文号为陕西省发改委[2005]740号文件显示,榆横煤化工园区240万吨甲醇制烯烃(MTO)项目最早由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和香港益业投资公司共同建设。
而一年后,“陕西省发改委[2006]677号”文件中,陕西省发改委同意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240万吨MTO项目一期60万吨甲醇项目,总投资229197万元,并由该公司自筹。在该文件中,该项目业主已经变成了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益业)。
陕西省工商局的登记资料显示:于2006年6月20日成立的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由中国化学工程与陕西益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陕西益业)共同出资。其中中国化学工程出资2000万元拥有10%股份,陕西益业出资18000万元持有90%股份,新公司由刘娟担任法人。
显然,香港益业并未直接投资,而是改由陕西益业与中国化学工程合作。原本“国企与外资合作”的项目变成了国企与私企的“强强联合”。颇具意味的是,早于中化益业之前两个月成立的陕西益业,其法定代表人也是刘娟。工商资料表明,该公司股东分别为生于1979年的西安人刘峰和陕西太兴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陕西太兴”),陕西太兴则成立于2003年6月10日,法定代表人为刘浩。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陕西太兴的法人刘浩正是刘娟的哥哥,而陕西益业的年轻大股东刘峰,是刘娟的侄子。
虽然股东不同,但香港益业、陕西益业、中化益业三家公司的法人均出自刘娟一人。更为蹊跷的是,根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到的工商年检资料,陕西益业、中化益业、太兴置业三家注册资金少则千万、多则2亿元的企业,其2007、2008、2009三年的纳税额总计不到16万元。
中化益业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显示,中国化学工程在该公司的实际出资额为零。而其所持有的10%股份,也已悉数转让给陕西太兴。至此,原本与国企共同申请的项目,已完全转为刘娟及其亲属的公司所有。
曾经的刘娟夫妇
在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中,刘娟“资本运筹能力”显露无疑。“中化益业”股东中,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为大型国有企业,但只持股10%,且双方约定,中国化学工程的股权只能转让给陕西益业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而后者的股权则可自由转让给第三方。
大型国企甘心向私企俯首,知情人士认为,这是刘娟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获知,今年50岁的刘娟,原籍陕西泾阳县,其父刘鹏是原安康地区平利县县委书记,后担任陕西省科协秘书长职务。
一份关于刘娟的简历显示,刘娟初中毕业后曾在安康文工团短暂任职,1982年至1985年到陕西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其后三年就读于深圳经贸大学涉外经济系。1990年至1992年,刘娟回陕西省政府工作。其后,远赴香港。从后来的轨迹看,其在香港颇为成功,并担任陕西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香港陕西省联谊会副会长。
曾与刘娟同时在省政府新城电大班学习的刘华钢介绍,学生时代的刘娟“心气很高”,加上能歌善舞,很引人注意。
一位曾与刘娟有过深入交流的人士表示,“刘聪明漂亮,看问题亦有独到的视角,她能盘活各种资源为其所用。”而另一方面,刘娟被评价为有主见。在《西部大开发》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刘娟曾尖锐指出,“政策互相打架问题普遍存在。主管部门交叉现象多,同样一件事情经常出现管理政策各异,这个主管部门同意了,却违背了另外一个主管部门的政策。这样就会造成很多事情停滞不前,甚至半途而废。”
刘华钢回忆,刘娟1982年入学前就在省政府办公厅当打字员,认识了后来的丈夫赵大新,赵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拉得一手好风琴,两人都是当时“活跃分子”。二人的结合被称为一段佳话。后来赵大新离开办公厅,官至省直机关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
上世纪80年代末,赵大新调往西安市雁塔区挂职,是雁塔区唯一个副厅级副区长。刘娟则选择了下海,1992年去了香港。而赵大新在雁塔区副区长的位子上一待就是12年。
一位曾与赵大新共事多年的工程师说,刘娟投身香港的最初阶段,做的是服装代理生意,但在赵大新的帮助下,很快就熟悉了资本运作。几年以后,刘娟以投资商的身体回到西安,开始投资房产领域,位于北大街附近的新时代广场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位工程师看来,刘娟出身干部家庭,各方面都很优秀,比较傲气,而出身教师家庭的赵大新则平易近人,聪明灵活。“刘娟锋芒毕露,而赵大新则绵里藏针”。就是这样一对互补互助的夫妻,在赵大新调到北京之后不久,却传出了两人离婚的消息。
谜团待解
随着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合同纠纷的升级,针对刘娟及其公司“借鸡下蛋”“借机圈煤”的质疑声四起。
与刘娟打过交道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香港完成转身之后,刘娟开始利用并进一步培植在内地的政府系统人脉。上述煤转化项目获批于2005年8月,但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被授权的“中化益业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将近一年后的2006年9月5日。该知情人士认为,此明显违规的背后肯定有人在操作。
亦有公开报道显示,2006年6月5日中化益业煤化工项目开工典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胡启立,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部长郑斯林,省委常委、副省长洪峰,国家煤炭部原部长张宝明,省政协副主席张保庆等出席,或致辞祝贺,或表示殷切期望。
刘华钢说,刘娟离开省政府以后,曾与他见过几面,但都未深谈,感觉比原来低调很多。
8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新时代广场8层,探访“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据刘娟的助理、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徐月英介绍,刘娟很少来单位,公司的日常工作由他人打理。
徐月英承认公司正与其他公司合作推进煤化工项目,但具体情况不便相告,而对于采访刘娟的要求,徐月英称须请示后才能决定。
至《中国新闻周刊》截稿时,未获得刘娟的回应。
榆林:失落的“中国科威特”
巨大的“黑金”利益面前,人性和权力都扭曲了
本刊记者/庞清辉 (发自陕西榆林)
榆林有1个区和11个县。在当地,以神木、府谷为代表的“北六县”和以米脂、绥德为代表的“南六县”,分别是富裕和贫穷的代名词。
贫和富的分界线就是地下是否有煤。
从榆林一路向北,到神木、店塔和大柳塔,再跨过乌兰木伦河到内蒙古上湾、到鄂尔多斯市,这条200多公里长的狭长地带被誉为中国的“能源走廊”。鄂尔多斯,被称作“大漠上的迪拜”;而榆林,则被冠以失落的“中国科威特”。鄂尔多斯市长曾揶揄榆林:“鄂尔多斯旁边有个市,资源比鄂尔多斯还丰富,但发展远比不上鄂尔多斯。”
陕煤集团董事长华玮也曾对媒体说:“两个城市的经济差距主要是因为两个政府思想解放程度的差距。”
经历了秦、汉、唐等帝王漫长统治的陕西,拥有悠久的历史,也一直延续了保守的官本位文化。贾平凹曾经说,陕北人聊天时爱谈中南海。
随着近些年地下煤矿的开发热潮,浸淫在官本位文化中的榆林人又投身于一夜暴富的狂喜中。各种势力卷杂其中,为“黑金”而博弈。
“求求你,开个煤矿吧”
“北六县”的煤是在1982年被发现的。陕西185煤田地质勘探队的报告说,在陕西神木、府谷、榆林78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蕴藏着877亿吨煤。1984年,新华社发出了一条电讯:“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榆林人记得这条朗朗上口的电讯。当地也传说当时邓小平下令要保护榆林煤田,要求只能在下个世纪最需要能源时才能开采。
那个时候,煤不值钱,煤老板远没有现在这么风光。买煤的人说只要块儿煤,不要面儿煤,煤老板就亲自下井去给人家挑块儿煤,挑出一车还要负责装好。“一吨五毛,一车两块钱。”经常代理煤矿官司、熟悉榆林煤矿史的廉姓律师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那个时候谁开煤矿谁赔钱。”当时乡镇管理矿权的干部,公章就在包里背着,沿着黄土高坡的沟坎,求着人来开煤矿,只要有人同意,立马掏出一张纸,划个范围,盖个章就是采矿证了,然后再去申请工商局的营业执照,不像现在是“先照后证”。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榆林的煤也才卖到十几块一吨,末期也不过二三十块。最主要一个原因是陕西的交通不好,往南下不去,向东要路过同样是产煤大省的山西,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很难借道山西,榆林的煤只能卖到甘肃和宁夏。
直到2000年,榆林人坐拥“黑金”,但仍穷得掉渣。廉律师的一个煤老板朋友,曾经坐拥7个煤矿,最后一共作价百十来万就卖掉了,还嘱咐他这个中间人一定把合同写严谨,省得买了煤矿的人反悔。现在,倒是自己的肠子都悔青了。眼下哪怕只有1个煤矿都富得流油,何况7个。
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樊家河村的樊占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意识到也许煤炭要值钱,1995年承包了村里十几亩荒沙滩办煤矿,每年交给村里2000块的土地费,期满后井口归村委会。1996年12月,横山县矿管局给其颁发了一个面积为5.81平方公里的采矿证。矿名为波罗镇樊家河村北窑湾煤矿,企业性质为集体性质,负责人樊占飞。在那个时期,大量的乡镇、乡村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矿山企业纷纷成立。
小规模矿山的发证权力归市县地方政府所有,而大规模矿山的成立,则需要到省或中央的矿产管理部门办理采矿许可证,并且采矿证的转让审批权还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因此,地方政府从控制权的角度出发,不希望小矿山联合成大矿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翻阅的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资料《我国探矿权采矿权发展简史》上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相当一部分的矿产资源需求,让乡镇的矿业企业承担了。这些非国有矿山企业大部分是以集体经济形式存在的,并且为私人所控制。
煤炭变“黑金”
1996年,《矿产资源法》修订,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矿业权取得是通过“双轨制”,即指从矿产资源所有人国家手中取得矿业权的方式存在有偿取得和无偿划拨或审批取得两种情况。但直到2004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施行时,矿业权的取得大多是以象征性的代价取得,甚至无偿取得。
自2003年以来,除了榆林,包括河北唐山、内蒙古的包头和鄂尔多斯、四川等很多能源丰富的地区,都掀起了个人成立公司圈占资源的风潮。
2002年以后,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逐步市场化,涨得超出很多人预期。加上2003年山西矿难频发,山西煤矿大整顿,全国中小煤矿先关闭再整合。而陕西的煤炭业却迎来了它的焕发期。榆林的动力煤煤质好,2003年以后,煤价从一吨100块一路涨至600块。
在榆林,人们更看重这一纸采矿证的潜力。2003年,赵发琦的榆林市凯奇莱公司与陕西省西勘院签订《合作勘查合同书》,联合进行详查及精查面积共计279.24平方公里的波罗——红石桥勘查区煤炭资源。
2004年年底,初步数据显示矿权区域内储藏着优质动力煤近20亿吨。赵发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不是后来出变故,我现在应该是百亿身价了,这可是二十亿吨煤,绝对好的煤。”据赵发琦介绍,在榆林,国企煤炭开发占不到1%,除了神华等少有的几个国企,都是自然人,多年前圈下的,且大多是集资。
榆林上亿的富豪很多。采访中,当地人经常给你举各种例子,炫耀他们的富豪。比如,在榆林市的神木县,身家上亿的富豪如果一个挨一个地站在一起,能站满整个县政府附近的广场;比如一个煤老板去西安买房,另一个煤老板在电话里通知“顺便给我捎上一柱柱”(所谓的“一柱柱”,也就是一个单元);比如有的煤老板在东南亚赌钱,一次能输几千万。
和山西相比,榆林的煤炭资源储量更大。据榆林市政协调研报告显示,榆林市矿产资源储量相当于50个大同矿区、100个抚顺矿区,约占全国总量的1/3。但是,山西的煤炭开发早,很多资源都已经有主。而榆林的开发很晚,有很多都是没有主的资源,所以,赵发琦说:“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的权力没有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的三分之一大。”
这里普通一个煤矿的价值,从80万卖到200万,到2000万,到1.8个亿,再到4个亿,翻着翻地往上滚。煤老板张合(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国土资源部门,管不了天,但地下搬不动的全归他们管,他们是管地球的。”
很多县级煤炭局长连任十几年,从来没有换过。除了部分官员入股煤矿外,张合一年在某些政府部门上“要花不少钱”,因为批准雷管炸药、处理越界开采和矿难等都要“关照”。
榆林的煤矿官司纠纷很多,曾经有人嘲笑当时正打官司的张合,“你是夹着包来打官司的,人家是提着麻袋来的,你别打了。”
套取煤炭资源
2003年10月,陕西省政府常委会决定,对由于省政府前几年已经给予一些煤田探矿权的单位,一律视作代表政府实施地质勘查,探矿权人无权处置矿权,其探矿权是否转让、转让给谁、如何转让,一律由省政府根据基地建设总体规划和转化项目落实情况作出决策。对在陕西落实的转化项目,由省政府统一配置相应的煤炭资源。
煤化工产业是煤炭深加工产业,是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涉及面广,工程建设复杂,实施难度大。这就提高了取得采矿权的门槛,而陕西省政府在门槛外也就有了选择权。
2006年4月,榆林市与正大能源化工集团签订了240万吨煤制甲醇及甲醇制烯烃(MTO)项目协议;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兖矿1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协议。2006年8月,陕西省政府把榆树湾煤矿分别配置给兖州煤业和正大能源搞转化项目。
“榆树湾煤矿是当时国资委特批给榆林的,但后来被划给了其他一些人,他们花了十几万注册了一个公司,打着正大的牌子,20多亿吨煤的项目就这么被十几万套走了。”曾经主管榆林市煤炭事务的副市长王斌说。
与此同时,2006年3月,陕西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110号文件同意中国化学工程、香港益业公司作为240万吨甲醇制烯烃(MTO)项目开发主体,进入“榆横矿区波罗井田”煤炭资源的精查。
作为陕西中化益业项目配套煤源的波罗煤矿储量丰沛,煤质优良,面积约340平方公里,地质储量约19亿吨,按正常预算,波罗井田价值可达上千亿。
两个项目异曲同工,腾挪之间,无非都是为了一纸采矿证。
早在2004年左右,在外人看来的一些正在磋商的大项目即将纷纷入驻榆林时,王斌就很反对,“其实那些所谓的大项目啊,都是一伙人找托挂牌的糊弄手法,为了骗取地方资源。”
当地一位煤化工项目的老总却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煤化工项目相比起来正规得多,却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拿不到配套的煤田。
有意思的是,上述陕西中化益业项目配套煤源的面积约340平方公里“波罗井田”,和赵发琦与陕西省西勘院签订《合作勘查合同书》的279.24平方公里的波罗——红石桥勘查区煤炭资源,大部分重合,而樊占飞当年代表村委会获得的面积为5.81平方公里的采矿区域又在赵发琦的探矿区域内——三个采矿证发展的历史于是就以这样高调的方式在同一片土地上迎头相撞。
这已就不再是樊占飞们和赵发琦们的“游戏”了。
还原陕西“行政抗法”事件
无论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其公信力都有打折之虞,而尤以更强势的行政权为甚
本刊记者/申欣旺(发自陕西西安)
“密函施压最高院”以及“协调会否决法院判决”,两起事件经媒体接连曝光后,使得陕西省在经历“周老虎事件”后,再次陷入全国关注的舆论漩涡中,这一次的主题则是“行政干预司法”。
事件发生后,陕西省方面成立了3个调查组进行调查。8月24日,调查组成员之一、陕西省监察厅效能室主任李献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查报告已经形成,由省政府办公厅具体负责。李献峰说,前段时间调查组曾召开会议讨论报告发布的问题,但此后由于他转而负责另外的事情,不知调查结果何时发布。
调查启动
8月16日,陕西省政府东侧阅报栏,行人正围着读报。戏剧性的是,阅报栏张贴的并非党报,亦非地方都市报,赫然张贴的是《南方周末》质疑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的报道,“最高法很生气,国土厅很淡定”的标题在明朗的阳光下异常醒目。
在陕西采访期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觉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口风明显收紧。陕西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岳喜栋对记者表示,“最近有规定,采访需要组织安排。”
陕西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与媒体联络室副主任谢泱倒是说得很好,“事情发生了就坦然面对,没什么需要捂的。”但对于省政府如何反应,谢表示自己刚出差回来,没有参与处理,尚不知情。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是此次舆论的焦点:两起案件中,它均被媒体指为“以权抗法”。
相关媒体的报道进一步将舆论焦点引向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该厅厅长王登记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诉苦”,“我所说的意思被曲解,很痛苦”。
电话中,王登记显得相当豪爽,并不掩饰其对媒体失望的情绪,但婉拒采访,“现在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成立了三个调查组正在调查。调查结果会跟媒体见面。到时候会有个说法。”
国土厅办公室主任汤鹏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半月前由省政府监察厅、法制办等组成的调查组已经完成对国土资源厅的调查和取证。”
《中国新闻周刊》从权威渠道获得证实,调查组由陕西省监察厅副厅长岳崇担任组长。岳崇为民进陕西省委副主委,接近陕西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记者,党外人士担任调查组长,更能凸显对此事独立调查的意味。
李献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横山械斗后,陕西省政府就成立关于此事件的调查组,后又根据案件侧重分设了三个调查组,其中监察厅从行政监察与是否存在违法违纪角度进行调查;而政府法制办则主要从法律角度对涉及的部门以及法律文书进行评估分析,公安厅则在械斗后第一时间赶赴横山械斗现场进行处理。
陕西省政府内部人士透露,横山械斗发生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赵正永就作出批示。赵正永在任常务副省长期间分管国土资源工作。另有榆林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8月中旬,赵正永在榆林调研,议题之一就是处理械斗案。
不一样的“真相”
导致这场风波的矿权纠纷发生于1999年。横山县山东煤矿(集体性质)原负责人樊占飞称,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合伙人李钊把采矿许可证上的采矿权人“樊占飞”变更为“李钊等人”。
2002年,樊占飞把批准这一变更的陕西省国土厅告上了法庭。此后在横山县、榆林市两级法院的一二审判决中,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均获胜诉。2005年形势逆转,榆林中院重审该案,国土厅败诉。2007年,陕西省高级法院驳回了国土厅的申诉请求。
今年3月1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组织召开“波罗镇山东煤矿采矿权属协调会”。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召开协调会的背景是因为樊占飞不断上访。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甚至给省政法委打报告,希望其出面解决。最终在省高层领导的过问下,仍由国土资源厅自己解决,因此有了后来的“协调会”。
这次协调会后来被新华社等媒体批评为行政干预司法,是搞“庭外审判“的样本。但接近陕西省决策层的人士认为,媒体报道断章取义,未能完全反映协调会原貌。
事件一方当事人樊占飞与其代理律师王西周称,准时到达会场后,他们被告知不能参加会议,在指定地点等候消息。王西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我们一直等,人家在上面开会。”
在王西周看来,这个时间足够做很多事情,“七八个小时的会,可以协调众人的意见。所以我们上去坐下以后,人家就做一个宣布。”
当日下午,省国土厅向他们宣布,经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及法律专家对该矿纠纷案进行解读,一致认定:第一,山东煤矿矿权与樊占飞、北窑湾煤矿、樊河村村民以及樊河村村集体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山东煤矿拿出八百万元给樊占飞作为招商引资奖励;第三,如果不服从这个结果,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求得法律救济。
事件被披露后,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顿成众矢之的,被指责为“行政干涉司法”,而另一方面,由于省高院法官的参会,也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公信力“打折”
“榆林中院并没有将矿井具体判给谁,如果判给樊占飞,他没有营业执照,进不了矿。法院只是撤销了原来的行政许可,但同时认为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国土资源厅职责所系。”王周户回忆此判决书认为榆林中院的判决颇为高明。
但王周户同时认为,榆林中院的判决给了当事人一个期待,使当事人有了一种非此即彼(不是李钊的就必然是樊占飞的)的想法。
出席“协调会”的陕西省高院行政庭庭长秦安祥以及主办法官葛迪也备受关注。有当事人认为,省高院派人到国土资源厅解释自己“到底判的啥”,大失颜面,司法公信力大打折扣。
王西周认为既然法院撤销了国土资源厅给李钊的采矿许可证,就应该属于樊占飞。在协调会上,王西周和葛迪甚至发生了争执,但葛迪并没有过多辩解。
西安一位长期从事矿产纠纷案件代理的律师则表示,“在利益面前,司法遭受到更严重的侵蚀。”
但法院内部人士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行政机关草率行事,最后却要法院来收拾局面并遭受公众指责。言下之意颇为委屈。
甚为微妙的是,此次事件的主要当事者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自始至终没有回应。对于公众“司法独立的讨论不应仅仅止步于能否执行的问题,而更应延伸到司法如何独立于权力和金钱之外”的发问亦无表态。
《中国新闻周刊》从权威渠道获知,媒体报道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干涉司法判决之后,最高法院相关主管领导异常重视,并直接给陕西高院行政庭庭长秦安祥打电话过问此事。
陕西高院在短时间内就此事向最高法院提交报告,就横山基层法院与榆林中院以及省高院的诸次判决理由进行了说明。其核心内容则是,法院依照法律仅有权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司法判决并不能代替行政许可本身。
尽管陕西省政府部门口风甚紧,但接受采访的人士大多认为,无论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其公信力都面临着利益的考验。前述长期代理矿权纠纷的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陕北流行的一句话是,你用塑料袋提钱(打官司),我用麻袋提钱(打官司),看谁打得过谁?
接受采访的陕西省高院某法官也坦承,在这种氛围下,就算法官再排除干扰,也无济于事,“一打官司就想着找关系,整个社会氛围如此,我们秉公办案又能怎样?又有谁能相信?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